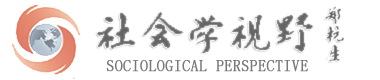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联系电话🏬:010-62511143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王铭铭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尊龙凯时娱乐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尊龙凯时娱乐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尊龙凯时娱乐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尊龙凯时娱乐积储的遗产,的��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𓀔,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尊龙凯时娱乐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尊龙凯时娱乐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尊龙凯时娱乐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尊龙凯时娱乐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尊龙凯时娱乐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