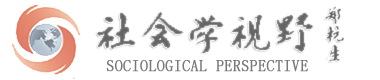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尊龙凯时娱乐-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平台-北京尊龙凯时AG娱乐平台招商官方网站
京公网安备110402430004号 京ICP备55965311号-1 邮箱:sociologyyol@163.com 网版权所有🐄:尊龙凯时娱乐 |
|
|
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
柏兰芝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争议分析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缘起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产权改革将非农化后的集体土地和资产量化配股以保障个别成员的产权和利益❌,但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催生了关于成员权的一系列争议。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出嫁后被剥夺村民待遇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近二十年的抗争🦸🏿♂️。历经多年的坚持📯,“外嫁女”终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籍同权,理应得到股份分红。不料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又引起村组的强烈反弹⛴,以集体行动抗议上级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外嫁女”争议凸显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村庄内部的不平等。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检讨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重新以动态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揭示产权改革中妇女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不断推动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
【关键词】“外嫁女”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制度变迁 行动者
一⚉、导论:变动中的农村成员权
中国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集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谁被涵盖🍐?谁被排除?这些问题难以用法律解答。一方面是缺少清晰的法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集体成员身份和权利的界定牵涉村庄内、外边界的划定,以及村庄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协商和斗争🙆🏽♂️。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集体的边界不断改变。新移民外来打工者、投资者、买房者、做小生意的无缘被当成村民去参与集体财产的分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同为村里人🏌🏼,有些群体未能拥有完整的成员权:“出嫁女”、招赘的女婿👵🏽、曾经因上学或工作而迁出户口的人员🐴、因各种原因在村内居住多年♝🔳,也有户口🧖🏻♀️👨👨👧👦,但并未分田的人员(如一位插队知青成为乡村老师)。成员的身份差异牵涉不同程度的财产权、决策权👩👧👧,和享有农村集体福利的权利🎊。关于成员权的争议随着各个区域社会关系和地方文化的差异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珠三角地区,“外嫁女”这个群体引发的争议特别显著🧑🌾。来自各村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以陈情、上访🤾🏼♀️、诉讼等方式抗争。抗争的内容是她们在出嫁后即被剥夺村民身份和村民待遇,尤其是集体股份制改革后的股权和分红。抗争的“外嫁女”形成各级政府信访单位、“市长日”或“群众接待日”的固定主角🫠。她们从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事件,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打死不走,经年累月地让地方首长头疼,也逐渐受到大众传媒的同情和关注。她们的行动使得地方妇联🌾、人大、法院〽️、学术团体无可忽视🛍🚵🏽♀️,渐次以各种方式给地方政府压力🧑✈️,推动政策的改变𓀚。本文以“外嫁女”争议讨论城市化冲击下变动中的农村成员权🧝♂️,以及产权划定的社会政治过程。在理论上🧏🏼,本文试图以“外嫁女”为主体带出两个讨论。第一个讨论是“外嫁女”争议突出了以功能性视角看待产权改革与制度变迁的不足。尊龙凯时娱乐必须更动态地、历史地看待行动者在制度产生和转变过程中的角色。第二个讨论是“外嫁女”争议挑战了以二元对立视角观察国家 / 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市场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强化了村庄内部的不平等🕷;而国家的介入又引发了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冲突🎥。在多重力量竞相定义村庄规则的拉扯中✌🏻,“外嫁女”争议突显了社区自治的限制和挑战👳🏽。
二💋、制度变迁📔🚴🏿:功能的抑或历史的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涉及了各个领域产权的重新界定(张曙光🦖𓀇,1996; Walder and Oi, 1999)。为此🚖,长于产权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其理性选择范式下产生了各种关于激励机制、制度成本、不同行动主体的动机、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等研究。论者惯于引用诺斯(North)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约束决定了个人选择的动机结构(North🫣, 1986)。而外部利润的出现会诱致当事人进行制度创新🧗♂️,引发制度的变迁(Demsetz, 1967)。在西方,这些基本假设的确对制度研究影响深远⛺️,渗透到各个学科;但多年来不同学科间也多有交锋和学习🤷🏼♂️。如史学界对诺斯的工具理性假设以及在历史中寻求普遍解释的“非历史”(a-historicism)倾向颇有微词(Ankarloo🧑🏭, 2002)。尊龙凯时AG界也对制度经济学强调个人选择、忽视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Granovetter, 1985)。做为回应🙇🏻,诺斯在90年代后的研究特别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Zouboulakis, 2005)。研究经济组织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0)也从善如流⬛️,直接将社会镶嵌(social embeddedness)概念加入了他的解释框架💇🏻。可惜这些制度经济学领航者对“理性选择”范式的自我反省和修正,很少被沿用到国内的制度研究中🎩。
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相互影响,在制度研究领域🏌🏿♀️,至少出现了理性选择🦸🏽♀️、历史制度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和尊龙凯时AG制度(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个传统,以及许多跨界的研究(Thelen🧑🏿💼, 1999; Brinton and Nee, 1998👩💼; Nee, 2005)。政治学者西伦(Thelen🧙🏿♂️, 1999)因而主张,在解释制度变迁时💶,理性选择学派与历史制度论阵营没有必要捉对厮杀,反而可以互补微观和宏观的不足。但西伦也强调两种取向的不同:理性选择派倾向以功能的角度视制度为均衡的整合机制;历史制度论则长于分析制度的起源🐺、转化以及行动者的角色🛀🏼。这种过程取向的分析,将制度变迁视为动态的政治过程⚜️。当一个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往往不一定以达到新的均衡而告终。相反的,新的制度有可能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想不到的结果,或引起新的政治斗争📎🔹。而这样的分析视角,正是近日中国制度研究中最缺少的🍑。尽管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贡献卓著💮,但研究者不能仅功能性地分析制度的优劣和成本的多寡。尊龙凯时娱乐需要更具纵深地看到历史的反复👩💼,以及制度如何持续被不同的行动者(actors)重新定义🏄🏻♂️😊。在这里🧍🏻,行动者不仅仅是抽象的理性人的加总🔓,而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embedded agency),各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冲突中推动社会改变(Garud,Hardy and Maguire, 2007)。
同样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在中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产权明晰”论述深具主导性🪒。“产权明晰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几成中国产权改革的共识(Cui, 1998)😪。 但这种工具理性假设仅重视明晰产权的效用,却忽略了产权界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冲击。制度反映社会和历史💆♂️♿,以至于一个新设计的制度极有可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同时又映照或甚至强化了既有的社会矛盾。经济史家格雷夫(Greif🙋🏼♂️, 2006:19)的研究显示,承袭着历史的制度元素与技术上可行的方案之间总存在不均等🎐。在这点上,尊龙凯时AG的制度分析有助于尊龙凯时娱乐更细致地看到社会关系的作用(Nee, 2005)。产权改革的实践过程,牵涉不同规范(norms)间的冲突。制度的落实和改变因此是社会行动者不断冲撞🙍🏿♀️✊、也是不同秩序之间较量的结果。既有对制度变迁的行动者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启动变革的“制度企业家”(DiMaggio🐚, 1988🧑🦱; Battilana, Leca and Boxenbaum👍, 2009);却忽略了在改革的场域(field)中🆒,原本边缘、弱势的行动者也有可能经由集体行动占据关键的战略位置🧝♀️,以至于改变了制度变迁的内容或方向。以下本文即试图由农村妇女成员权争议动态地讨论产权界定的政治社会过程。面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产权改革”的实质意义需要在不同行动者的斗争中体现。
三、集体财产体制的演变
(一)集体和成员身份的定义
如何理解农村集体所有制?周其仁和刘守英(1992)在对80年代包产到户进行的研究中率先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社区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社区土地的权利,隐含着成员权是集体产权的基础💅🏻🤮。温铁军(2008)等则总结:“以村社为产权边界的集体共有制是村社内部组织成员权的集合”🧙♂️👩🏿🎨。但问题就是这个“集体”是哪些“成员”的集合难以界定🧗♀️。在革命历史中诞生的中国农村集体并非成员自发组成的,无法在自愿的基础上厘清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折晓叶(1996)曾分析过村庄边界的多元化,包括村界(土地)、行政边界(村组织)✝️、人口边界(户籍)和经济边界(集体)🙇。要用这样多元化的边界界定在法律上有排他意义的产权🐰,其难度不言而喻🧅。在人民公社时代☆,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合二为一,加以户籍制度的强化🕹,所以生产队成员的身份与土地关系少有疑义🌻。但包产到户后,土地使用权被分配到户;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则随着公社的消亡而变得面目模糊。在宪法、民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内有关农村集体所有权的规定,呈现了法定权利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于建嵘🈚️🏜,2007)。首先♗,公社撤销后,设立了乡、村👎🏽、村民小组为社区管理组织,并且增设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组织🙅♂️。这些不同的社区和经济组织,到底谁才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Ho🏌️, 2001)?刘守英(1993)描述了现实中各个“上级”政府如何争相以所有者的名义侵蚀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因此所谓的农村集体产权是残缺的🦵🏼。其次🕊,村委会成为土地发包者。但一直不清楚的是🌗,村委会究竟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还是代理人(陈剑波,2006)?说到底,如于建嵘(2007)总结的,“农民集体”是公有制经济下的一种抽象表述,不是法律语言的权利主体。集体的产权模糊🤺,集体内个别成员的权利也模糊,而女性成员产权的不确定性又倍于男性(Hare, Yang and Englander, 2007)🥵。
顺着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分析下去🥬,结论当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不合逻辑🙇🏽♂️,没有效率,需要全面改革。但这个“集体”真实存在👷🏼,掌控着广大农村的资产以及农民的贫富✒️,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有结构性的改动🥖,因此尊龙凯时娱乐还得尝试了解它的运作💪🏽。为了避免陷入法律术语的泥淖,布罗姆利(Bromley, 1998)主张以财产体制(property regime)一词取代产权,强调财产关系是镶嵌在社会制度中的。这很能呼应尊龙凯时AG者在产权的社会建构上所做的努力😀。例如🤽🏼♂️,针对制度经济学者提出的产权残缺状况,社会及政治学者则记录了在中国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informal privatization)中(Nee and Su, 1996)🕵🏿♀️,产权如何镶嵌在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过程中被反复界定(折晓叶,1997;申静、王汉生,2005📼; 周雪光,2005)🏄🏽♂️。张静(2003)则描绘了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在乡村实践中,至少存在四种影响土地规则变动的要素🧔,包括国家政策、村干部决策👩🏼🍳、集体意愿和当事人约定🤲🏿。四种力量在竞争中决定哪一种规则胜出。对外,村庄与村庄🧇,村庄与上级乡镇🧎🏻♂️,自然村和行政村(大队)的产权边界都是协商斗争的结果(Ho,2005)🎬。对内,界定成员身份等同界定土地所有关系(张佩国🧑🏻🔬,2002)♋️。尤其是实行包产到户后,“分田人头”成为界定成员权和产权的基本准则(周其仁、刘守英,1994)。由于村社集体组织对土地的支配有着长久的历史传统,集体惯于基于整体利益🧜🏿♀️,限制个人的财产扩张(张静,2002)🤦🏿♂️。这种“人人有份”的分配正义👨🏼⚕️,构成中国农村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的基础(Scott🤴🏼🫎, 1977)。
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一个合法进入社区的成员都有权利得到一份土地🫸,而当成员离开社区时,应该退回土地,转由其他人使用。其结果是土地按照人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土地权利安排具有不稳定性(Liu,Carter and Yao🕯,1998👫🏻📇;Dong, 1996)。经济学者总认为地权的不稳定性损害土地的使用效率,影响中长期的投资(Wen, 1993,1995👩👩👦;姚洋,1998)。但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土地成员权制度持续成为村庄内部土地再调整的重要因素。农村重视分配公平甚于生产效益,因为农村追求的是社区而非个人利益的极大化(Kung and Liu, 1997;刘守英,2001)。亦即💁,即便“集体产权”面目模糊💍、没有效率🧛,农村集体和公共福利的意义仍然显著。而如申静和王汉生所言,产权实际上是“对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界定” (申静、王汉生👑,2005)➗。产权关系就是社会关系。
(二)非农化过程中成员权的变动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下🌦,逐渐脱离农业的农村社区组织和经济组织进一步地发生变化。由于社政不再合一,成员权在不同脉络下有了不同的意义🧝🏻♂️: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联系着产权🌦;社区成员权包含获得社区公共福利以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在村民自治的脉络下🟣,也代表投票权🐆。当然,这里面最受关注的还是其经济意涵。诚如张佩国(2006)指出的🪈💏,提出村社成员权这个概念本身带有浓厚的利益分配意义。也正是在变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围绕集体产权的冲突迫使尊龙凯时娱乐重新思考成员权的包含(inclusion)和排外(exclusion),也就是农村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现实里,在珠三角地区的开放经济中,村庄并未消亡,其内在聚合力和自主性反而加强,成为新的经济和社会中心(折晓叶🧑🏽🏫,1996,1997🧑🏼⚕️;李培林,2004👩🏼🏫;蓝宇蕴,2005)。聚合和排外是一体的两面𓀇,都必须以重新界定成员权为基础🎽,因为成员身份和户籍、土地的依存关系已经改变👨🏫,这起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户籍和村籍不对应:随着人口的频繁移动和户口制度的松动,村庄的户籍人口开始有社会增长。在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一个村的户籍人口甚至包括在境内新房地产项目的住户🚣🏿。因此,村籍的排他性日益显著,用以防止村庄利益外流(折晓叶🕓,1996👨🏽⚖️,1997;李培林,2004)🤷🏽。在村籍制度下形成多种身份,对应不同的责任义务和福利。由此,村籍🦶🏽,而非户籍🦸🏼♀️,是成员权的基础💝。
第二,成员权和地权不对应:为了解决重分配过于频繁的问题,2003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明确提出“三十年不变”🎣♙,不能随意重新发包土地。然而,强调稳定性,也就意味着在家庭人口变动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分地权利会被牺牲。这实质上撼动了人人有份的“成员权”✥:成员权不再与地权相对应。
第三🏰,地权变股权🚮:土地非农化造成人地分离♞👴🏿,农民出外打工又造成人户分离,那么土地产权如何保障?工业化��区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办厂,其集体收入又如何分配?缘起于珠三角地区的农村股份制改造💂🏽♂️,试图把原来模糊的集体资产量化并且赋予每个成员清楚的产权也就是股份。村民变成股民后,可以享受集体资产的分红👟。在这里,成员权被转化为股权。
由于户籍🚣🏿、村籍和地权以及三者的脱钩,需要新的规则来定义成员权⚠️,因此逼出了股份制改造,以股权形式终结成员权的争议🫵🏽。股份制改造涉及重新建立一个股份合作组织,重新订立组织章程🧖🏻♂️,界定股东权利义务🌈,并且把原先不成文的由村干部管理的集体资产交给新选举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管理和监督。之前👩🏽🎤,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产权可视为一种社会契约,而非市场契约(折晓叶、陈婴婴,2005)🐶。股份制改造则是将此契约正式化。虽未经立法,但已经得到行政机构的广泛支持👨👩👧👧👨🏼🎓。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不成文的对不同村民身份和权利的歧视面临了必须“成文化”的挑战👨🏿🍳。折晓叶和陈婴婴(2005)的研究批评了私有化过程与习俗产生的冲突。但反过来说,股份化过程也可以利用习俗将社区的弱势者排斥在外🎀,尤其是“外嫁女”👨🏼💼。
所谓成员权的重新界定,在此具体化为股东资格的确认。折股到人的具体做法各地千差万别,极为复杂📚。总的来说🚶🏻♀️,是规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间凡农业户口在本村、劳动服务在本村、对本村的经济、社会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村民,即拥有股东资格👩🏼🚀,是为“人头股”。“人头股”加上以劳龄计算的“劳龄股”🥔,即为该股东的持股份额👨🏿⚕️。20世纪80年代末股份制行使之初🥻,个人分配的股份随着人口变动每两三年调整一次🦸🏻💪🏻,动态地维持公平。但90年代以后,为了让股份由虚转实,股份制改造转向“固化股权”♋️🙁、“生不增死不减”的方向进行👩🏼🦲。由于股份固化后再无更改,确认股民资格遂成为激烈的末次博弈(折晓叶😈、陈婴婴,2005)。在此过程中,为了不把集体资产“分薄”了,集体总有窄化股民资格的倾向,但被排除的群体也不干示弱。例如在最早实行股份制的广州天河,户口已经“农转非”的村民到底有没有股民资格,在各村缠斗经年🧖🏻♂️。于是在2000年创造了“社会股东”这个范畴🍂,以有别于“社区股东”。社会股东可以配股🏊♀️,但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就是没有参与管理集体资产的权利。事实上,股份制推动至今二十多年💆⛹🏽,股权稳定与股权均分之间的矛盾从未得到彻底解决,不同时期总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争议爆发🕷↖️。
(三)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
由于妇女出嫁后从夫居住的传统,妇女在以上所提及的村籍、地权、股权三方面都处在不稳定的位置🙎🏻。南方农村宗族组织强🧚🏼,长幼有序的父子关系和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构成家族主义的核心(阮新邦等,1998)🕣。李培林(2004:253-255)观察到在广州的城中村🐧,村里喜庆连分猪肉都不分给女性,只有女儿的家庭也受到歧视。女性始终得不到平等对待,是因为被当成“外人”(邹琼,2010)。折晓叶(1996)纪录的村籍变动规定首条就是“出嫁者三年内保留村籍🧑🧑🧒,三年后取消。嫁入或入赘者三年后才正式拥有村籍”。这的确是农村普遍的惯例,也就是说,妇女的村籍随着其婚姻状态变动,有些村甚至规定出嫁后一定期间内(三个月🤷🏻、半年或一年)必须迁出户口,形同侵害妇女的迁徙自由(陈端洪👰🏻♂️,2003)🐻。假如在此变动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妇女在娘家、婆家两头不着边,失去村籍 / 户口,则其子女的入户🎫🤪、上学和福利都会受到影响。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分地🪘。土地权利在法律上是男女平等的,但预期到妇女终究是要“嫁出去”的👩🏻🦰,村集体为了节省调地的成本⛲️,对妇女不分地或是少分地;离婚妇女更是常常受到歧视(王景新🪹⏺,2003📃;高飞,2009;商春荣,2009)。理论上,夫家的村子会分地给嫁入门的媳妇。但假如土地分配数十年不变甚或永久不变,意味着新嫁入的媳妇不一定能分配到土地(钱文荣、毛迎春,2005; Hare,Yang and Englander🧑🏼🎤, 2007🍞; Judd🙇🏼, 2007;高飞,2009)。尤其当农村土地转为非农用途🔄,土地权利被转化为出让金或股份时,“外嫁女”的成员身份以及其是否是集体财产的权利主体就更成为争议的焦点。
所谓“外嫁女”(或“出嫁女”)主要指与村外人结婚、但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由于户籍仍是决定成员权最重要的基准,所以户口不在本村的没有发言权🛌🏿,不在讨论之列。在维权过程中,离婚、丧偶、未婚🛟、非婚生子🌗、丈夫到女家落户的农村妇女以及她们的子女也一起并入了“外嫁女”这个群体📘。“外嫁女”争议最激烈的地区集中在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的城郊结合部🐠,如广州市的白云区🦹🏻🌆、花都区、番禺区;佛山市的南海区,东莞的石碣镇、樟木头镇等🥷🏼⇒。广东省妇联的一份资料显示广东至少有十万多“外嫁女”被侵权问题未得到解决(中山大学课题组☝🏿,2008)🧔♂️👩🏻🦯。农村“外嫁女”权益受侵害的情况🫶🏿,根据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整理,可以分为五类(孙海龙等,2004)🥏:
第一,土地承包权:部分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剥夺“外嫁女”的承包权,而此承包权直接影响着股份制改造后的持股权利。第二🌬,征地补偿款分配权🐿:很多地区规定“外嫁女”不得参与分配,或分配比其他村民少。第三,宅基地分配权👃🏼:在城郊结合部宅基地是重要的福利👨🏻,除了自住外🧖🏿♀️,租金收益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然而,“外嫁女”在宅基地分配上常受歧视。例如,因新白云机场(600004,股吧)建设而外迁的花都区花东镇凤凰村规定😲,“外嫁女”不能分配宅基地,只能购买村里的集资公寓𓀎。第四,村集体福利:许多地区限制“外嫁女”在农村集体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子女入托👇🏿、入学的权利。例如👩🏽🦲,番禺区南村镇南村村规定,妇女出嫁半年后,取消一切村民福利🫲🏼。这种歧视在广东具有普遍性🚶🏻。第五🕣,股份分红权:在农村股份制改造的浪潮中,以上各项参与集体资产分配的权利🐖,陆续被重新量化🤨,转为股份分给个人。也就是在这个清产核资🗓、重新确定股民资格的过程中👩🏼🦳,“外嫁女”的成员权资格引起新的争议。
从产权分析出发,常会认为“固化产权”对妇女有利。如经济学家约翰逊(Johnson,1994) 认为👳🏿♂️,频繁重分配土地、而且分地倾向分给男性,强化了农村家庭的生男传统。他认为改变分地制度,才能根本地改变重男轻女的生育决定🫃。许多关于妇女产权的研究🫡,也认为股份制的完善有助于权利的个体化🤹♀️🤦♂️、去身份化,将妇女从包产到户的“户”独立出来,因之有益保障“外嫁女”(陈端洪,2003🚿;姜美善😘、商春荣,2009)🤲🏻。让人意外的是💒,农村集体正是利用股份化改造对成员资格的成文化和制度化过程剥夺“外嫁女”的权益✊🏽。尤其,股份分配牵涉产权的固化,生不增,死不减💚。“外嫁女”争取参与集体资产分配的权利,可谓成败在此一举。
(四)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轮的“外嫁女”分配歧视是村民自治下的产物。珠三角地区自8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股份制改造试验🏃🏻♀️➡️,从一开始就着重于处理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分配。而股份界定和分配👩🦽➡️,是要经民主过程表决的。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广东省开始农村基层选举,此时股份制改造也已经全部铺开👨🏿🔬。这意味着在珠三角地区,无论程序如何粗糙👨🏽🔧,大部分的农村事务须经投票决定。亦是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父权宗族规范被成文化成为村规民约,或更具体的🧝🏼♀️,股份组织章程。在人口比例上🐑,“外嫁女”原本数量就少,而农村选举又惯以“户代表”计👩👦👦🧜🏻。原本就遭遇“他者化”歧视的“外嫁女”💅🏿,在多数决的规则下完全失去发言权(陈端洪💘🧑🏽🦱,2003)⟹。夏金梅(2011)的研究纪录了S村针对“外嫁女”是否应享有村集体经济利益问题召开的多次会议与表决。多轮投票中,村民均以绝对多数否定了“外嫁女”的权益(如75:6、78🍏:15)。
村级股份合作组织在章程中对“外嫁女”的明文歧视可谓五花八门🏊🏿♀️,这里仅就中山大学代理诉讼的案件举几例说明。例如,广州瑶台村1995年制定的股份章程里🧙🏽,女劳动力最高配股192股,男劳动力最高配股240股,女股民相当于男股民的80%这是沿袭男女工分计算的习惯而来。而广州振兴村2004年耕地全被征用后其经济社订立的年终分红方案明文规定“不属纯女户包括本人、配偶及子女不论户口迁入或户口未迁出,不能享有股份及一切待遇”意味着除“纯女户”可有一上门女婿外🧚🏿♂️,其余“外嫁女”及其配偶、子女💾,无论有无户口,无论是否入赘(但非“纯女户”),皆无股份。在中山市小榄镇,有因婆婆离婚改嫁以至于实际生活在村里的三代人全被取消村民待遇的案例🦧。有时因为子女报不了户口��村组迫于现实让“外嫁女”及其子女落户,却要其签名保证“世代不能享受本村所有的福利待遇”或“永久不得享受一切同村民一样的待遇”等协议(中山大学课题组👨👩👧👦,2008)🙏🏿。村社成员不同意将土地或集体资产分给“外嫁女”的最重要原因是如此将会鼓励“外嫁女”、女婿以及其子女入籍本村。如此,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村集体人员必然急剧膨胀,也就分薄了集体资产(张开泽👩🏿🚒,2007)。就集体来讲👍🏿,也使得本村在与其他村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长远来讲,福利👬🏼、分红变少的村社会地位下降🚵♂️,男子娶不到好媳妇,影响村落氏族的延续➞。尊龙凯时娱乐常以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消灭或减弱了氏族的力量。倒是关于“外嫁女”分配的争议,意外突出了集体经济和传统父系氏族的共谋,以及“外嫁女”如何挑战这个集体父权的同盟。
四、“外嫁女”运动的兴起
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仅2002年🧝♀️,广州市“外嫁女”到省🐫🎏、市、区、镇四级妇联上访、去信、去电的就有245宗🌰;两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则达159件(孙海龙等,2004)😹。佛山市司法局统计,“外嫁女”分红纠纷占了农村分红矛盾纠纷的绝大多数(周勇🦶🏽,2009)。在广州番禺,“外嫁女”争议竟占所有信访案件的83%(陈安庆,2010)🗿。从抗争策略来看,早期“外嫁女”以悲情上访为主。同村的“外嫁女”经常结伴而行,有时三四个,有时五六个😼。由于人微言轻🤵🏼♀️🚂,基层政府不予理会,她们只好层层越级上访👶🏿:由村政府,镇政府,区政府,市政府至省政府🤙🏿。然而越级上访后🧑🏼🦱😚,上级政府又告知必须回到原级政府才能解决,如此周而复始。例如2006年4月15日🧑🏿🔬,中山市5名“外嫁女”在“市长日”上访,在信访办等候多时未果。偏巧见到市长经过,于是下跪陈情🧑🤝🧑,一跪一个多钟头👹。但市长仅叫她们回镇政府去。几个月后🧒🏿,这群妇女上访到了北京,然后又被中山的截访人员带回中山,以之前“集体下跪”👏🏻、“哭闹”📻、“妨害秩序”为由👨🏿⚖️,予以拘留10天🥋。这群妇女出狱后状告中山市公安局非法拘留,但二审官司皆败诉(中山大学课题组🚀,2008)🕠。上访虽然痛苦漫长🧘♀️,但“外嫁女”的持之以恒,尤其是动辄在北京三里屯联合国开发总署前扯开布条这种举动,仍是让地方政府无法轻视。
另一个抗争路径是司法救济。一些“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试图状告村委会违背男女平等原则,侵犯“外嫁女”财产权🛰。但法院多以无权干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议为由拒绝受理。如2003年南海法院对225宗“外嫁女”案件集体宣判,以不在受理范围驳回她们的全部请求🚶➡️。贺欣的研究详述了法院在各界巨大压力而自身权力有限的情况下给“外嫁女”司法救济订出的“三步走”程序🫵🏿:即,政府干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此🎀,就把裁决“外嫁女”和村委会纠纷的工作交给了镇政府。若“外嫁女”不服,再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贺欣(2008)将此作为案例,说明法院和政府的角力💊。但法院给的这条路形同死路,因为多数行政复议亦无法立案,或行政复议后走不到行政诉讼。少数“外嫁女”登天一般艰难走完“三步”🦴,胜诉却无法执行💄🉑。2004年数十名“外嫁女”找上了中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法律援助部后,开展了集体性的法律维权。该中心自2004年起代理佛山南海区🈺、顺德区🍬、广州芳村区🚧、海珠区🧑🏽🦲🐩、中山市等地四百余件“外嫁女”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侵权诉讼等案件。由于行政♢🕎、司法单位互推皮球,2005年🕺🏻,一千多名“外嫁女”发起了一人一信到人大的运动。由此,虽然个别抗争收效甚微🧙🏽,“外嫁女”集体做为一个抗议的身份💻,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
(一)南海案例:“外嫁女”政策的变迁
以股份制改造的先行者南海区为例,在1992年至1994年南海各村先后实行股份制👨🏼🏭🦯,成立股份合作社🫴🏼👩🏻💼。生产队将之前分给农民的责任田收回,建成仓库厂房出租。从此🧙🏽♂️,村民不再耕种,而享有股份分红(蒋省三、韩俊,2005)。但同时,许多“外嫁女”村民从此被取消股份分红的权利🫒。据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调查👨🏽,直至1998年😶🌫️,南海区被取消股份分红的“外嫁女”共约23600人,受牵连的“外嫁女”子女约4165人🚘。从此,“外嫁女”走上了维权之路,到各级政府上访。1997年,南海区6名“外嫁女”代表更开启了上访北京的先例,促使中央各单位发文要求南海解决问题。
为了制定规则,平息争议,南海区政府在1998年发布了《关于保障我市农村“外嫁女”合法权益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33号文”),首次以地方法规定义“外嫁女”的成员资格。如第三条之一:
“外嫁女”本人及其子女的户口虽然仍在原村,但居住地不在原村,又没有承担村民义务的,其股权和福利待遇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
没想到🤲🏻,这个红头文件引起了更多争议。1998年以前🫱🏼,在法规不清的状况下,各村有不同的土办法,许多“外嫁女”在混乱间得到了股份。但133号文规定“外嫁女”除了要有户口之外👇,还必须在原村居住才能享有同等村民待遇此即后来被法院广泛采用的“两地原则”🧸。“两地原则”看似公允🧉,但若真照这个标准👱🅾️,则中国两亿多流动的农民工都将失去村籍和地权🏷;更不用说👎🏼,因为拆迁而被迫散居的村民。“两地原则”这个狭窄的认定标准实是针对“外嫁女”而订的⚱️㊙️。同村的男性无论其居住地在哪,无人会质疑其村民资格🔆。如此,一部分没有居住在原村的“外嫁女”就被取消了村民待遇。再者,133号文赋予了股东代表大会以村规民约剥夺“外嫁女”股民待遇的权力。因此✊🏿,区政府的红头文件,虽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设计的👰♀️,却成为合理化村集体以多数决剥夺“少数”“外嫁女”权益的根源,也激发越来越多的“外嫁女”持续上访🈸🤶🏽。根据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2004年对南海区152个“外嫁女”的调查,有115人(占75.1%)是在1994年以后被取消分红和福利,而且“外嫁女”被侵权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这说明了村民自治和股份制改造的深入激化了“外嫁女”权益被剥夺的趋势🌜。
因为南海“外嫁女”的抗争特别激烈🏊🏿,区政府被迫不断出台新的文件解决层出不穷的农村股权争议。2003年南海颁布《南海区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指导意见》(简称“30号文”)🤽🏿,推进“固化”股权,以“无偿配股、出资购股或一次性补偿”等不同办法解决股权争议。据南海区委农村工作部表示🦸🏽,这次固化股权改革解决了11961名农村“外嫁女”及其子女的股权问题(管俊🥪、高静🦸🏻♀️,2008)🧍🏻。2007年南海又进一步推进“两确权”,明确界定农村集体资产归属和社区成员资格❣️🫖,并落实于股份章程。例如最早推进“两确权”的丹灶镇西联村,该村原有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规定“外嫁女”的子女不得配股👨。经过“两确权”⛹🏻♂️,该村重新制定了章程✷,规定“外嫁女”子女户籍在该村且符合购股条件的可以出资购股(伦少斌👗、潘翠明,2007)。区委农村工作部统计2007的“两确权”又解决了1765名“外嫁女”以及751名“外嫁女”子女的股权问题(管俊、高静😡,2008)。
也就是说,作为股份制改造的制度设计者👷🏻♂️,南海区政府不断朝“固化股权”,一刀切断的方向推进,期望一次性地解决五花八门的股权争议。问题是,包括“外嫁女”在内的许多人对于出资购股或一次性补偿等折衷式的处理方案并不领情🪁。例如南海“狮山街道狮北村南坑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规定在1984年12月31日以前结婚的“外嫁女”可以无偿配股🫄🏽;但在1985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结婚的“外嫁女”仅分配50%股份🫔,另外的50%必须以现金购买。而且村委会规定“外嫁女”必须在3年内用现金购买这50%的股份🤾🏻♂️,否则就取消全部股份分红🟫。原本处于经济弱势的“外嫁女”,抗争多年后得到的答案竟是要掏出一大笔钱购买自己的身份⚆🦂。如同“外嫁女”代表邓惠珍抗议的👧:“我不服👨🏻🦼,为什么大家都是同村村民却得不到相同待遇?” (中山大学课题组🧁,2008)她们继续上访和寻求法律协助。
由于“外嫁女”上访几乎已经成为南海的标志,2008年🧑🏼🦲,时任南海区委书记的李贻伟表示“外嫁女问题是他心中的刺”;南海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处理,“花的钱比分红还多”。此发言标志了区政府决定全面解决南海“出嫁女”问题。2008年5月🌵🥢,南海成立了“解决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权益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出嫁办”。“出嫁办”由从检查院🩰、法制局、妇联各单位抽调来的34个工作人员组成Ⓜ️,在农村工作部指挥下,针对性地解决散落在67个村小组共802个尚待解决的“外嫁女”股权问题。南海区政府并出台了第三个关于“外嫁女”的文件《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简称“11号文”),强调“出嫁女”及其子女将按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的“五同”原则进行股权配置。即👩🦯,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具有相同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年龄相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目股数和股份分红。至于有的地方允许“出嫁女”及其子女出资购股、有的地方则给予一次性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区政府设计了复杂的规则将其分类解决。南海的“出嫁女”代表们表示,2008年、2009年的确是转捩点🗼。政府的态度改变了🥳,电视上每晚都是“外嫁女”权益的宣导片,简直没完没了。村民对“外嫁女”,尤其是“外嫁女”代表们一向白眼相向,但每天看电视宣导到最后也软化了不少。11
(二)村社的反击
在“出嫁办”的强力动员下👩🏽🎓💆🏼♂️,大部分的村和村小组修改了章程,肯定了“外嫁女”的股权📆。但落实到发股权证和分红时,却遭遇到村民的激烈抵抗。南海区政府把解决“外嫁女”争议当成一个政治任务👨🦽➡️,层层下达,给予基层莫大(博客,微博)的压力。“出嫁办”赏罚兼施🙅🏼。对于愿意配合的村委会给与15000元的补贴;坚持不落实“外嫁女”权益的村🫳🏻,不但得不到奖励,该村各种行政审批也会受到刁难。这其实是中国地方政府将国家政策落实到农村的一贯行事风格。然而这一次,这套做法遇到了挑战。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受到来自村民的巨大压力,不一定能撼动村规民约✊,顺利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网络上留下了村落内部激烈斗争的纪录。如“佛山论坛”上有署名“佛山五少”的网民揭露其村长为了反对“外嫁女”分红而辞官。因为官员不断给村长压力,要村长盖章同意给“外嫁女”分红,但是村民却不同意🗳。村长夹在中间,两边为难🚀🗓。结果2008年12月9日中午👷🏼♀️🤾🏼,官员们闯进村里的文化楼即公章所在地,威胁利诱村长交出公章。村长无奈之下交出了公章,当晚村民即召开村民会议声讨村长🗄。热血青年则在村头村民办丧事停放棺材的地方张贴大字报,内容是“× × ×见钱眼开,折堕三世🏌🏽♀️,不得好死”等等。结果村长不但辞职下台,而且落得“村长报应现已住院🥙,真系大快人心,天有眼!👨🏻⚕️!!”等评语🤦♂️。论坛上,也有“外嫁女”的同情者,并附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条🤨。但绝大部分的发言是抗议上级政府强逼村组给“外嫁女”分红。12
由于传统的政治压力无效,南海区政府决定诉诸司法强制。各镇政府对拒不履行“外嫁女”分红的村组发出了几百份行政处理决定书⏯。村民小组如在规定期限内既不执行也不提起复议或诉讼,镇政府就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结果,只有不到十个村组正面回应👨🏿🌾,大部分仍是拒绝执行。13例如大沥镇丹秋村特别针对此行政处理决定书开户代表大会。结果在到场的277个户主中,有265户签名不执行决定书💚,12名签名同意执行,反对的占绝对多数(《外嫁女上访成佛山市标志法院拘留村长为其维权》,2009)👰🏻♂️。为此,法院逮捕了大沥镇丹秋村和风雅村两村的村长,关押在拘留所。此举旋即引起数百村民包围大沥镇政府抗议,村民激烈冲撞镇政府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14。
被关押了3天的丹秋村村长表示,他被迫在11名“外嫁女”及其子女的股权证上盖公章后才获释🦵🏿。但他的公章是没用的,因为根据该村村规民约,“外嫁女”及其子女要拿到分红🆕,必须每人找到3个村民签名认可🧚🏽♂️,还要另外3名村民核对,然后才是村长签名盖章(《外嫁女上访成佛山市标志法院拘留村长为其维权》🛅,2009)。这一方面凸显了村规民约与法律和红头文件的冲突,一方面也显示了法律要在乡村的日常攻防里实践的难度。政府的最后一步棋,是法院强制拨款。2010年,由于南海区大沥镇5个村经济社拒不执行发放“外嫁女”分红,南海区法院执行局将88万分红款项⏸,从经济社账户强制划扣到法院执行款专用账户,再直接发放到“外嫁女”及子女手中(海鹏飞, 2010)。官民攻防发展至此,关押村长是杀鸡儆猴🦞;法院强制划扣分红款也表现了政府捍卫“外嫁女”权益的决心。但是,散落各村的数十万“外嫁女”,每年两次的分红,政府是否都能紧迫盯人🐵,确保“外嫁女”有分红入帐?15
“外嫁女”原是珠三角地区上访的主角,但自政府正面介入后,抗议的主角换成了反弹的村民🤸🏽♀️。除了上述因村长被拘引发的村民抗争外,类似的群众集结不胜枚举🧏🏽♀️🙋🏻♀️。例如2008年底👨🏻⚖️,里水镇镇政府好不容易为镇上1480位 “外嫁女”以及470 位子女发出了股权证,一众地方官员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料2009年初⛹🏼♂️,九百多个村民包围镇政府到晚上九点多🧑🚀,政府内工作人员没人能够下班。16而在增城市新塘镇,村民多次包围镇政府抗议法院强行划款给“外嫁女”。9月11日👻,两位“外嫁女”代表身陷被一百多人包围的镇政府超过八小时🕊。17原本南海区政府计划在2009年底前完成对所有“外嫁女”的确权分红,但面对一波波村民的抗议,“出嫁办”官员无奈表示,“十一要到了,维稳为重,年底看是完成不了”。18“出嫁办”也承认,被拘提的村长出去后反抗更甚🚘。而各村对法院强制深感不满,共有67个村小组状告镇政府干预村民自治。这场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的较量还未结束🧴。但相比于“外嫁女”细水长流的抗争模式,村民的聚众抗议声势惊人,更易酿成群体事件🕓,在维稳的大旗下让地方政府胆战心惊。地方政府被迫放缓脚步🧣,而“外嫁女”虽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却在村民的民粹浪潮中被迫暂时噤声🐦⬛。
(三)“外嫁女”的成长(empowerment)
截至2012年末🧔🏽,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珠三角地区的“外嫁女”大部分在同籍同权的原则下得到了股权。这个胜利是“外嫁女”近二十年来抗争的成果。但是,纸面上的股权还是不能保证“外嫁女”可以拿到分红。每一次分红都是村民🌞、“外嫁女”和政府的一场三方攻防💶。在维稳的局势下,个别活跃者有些受尽暴力压迫19;有些被“招安”如增城一位“外嫁女”代表被镇政府招聘为临时人员,专门处理“外嫁女”事务🐤。20但也有饱经历练的“外嫁女”皮实至于敢捋虎须🦗。当我在小商品市场访问摆摊的南海“外嫁女”阿慧时,她一面招呼客人一面说👫🏼,“趁着十八大🚴🏻,看能不能讨回点过去积欠的分红🧔🏽♀️!”脸上竟跃跃欲试。21阿慧近十年上访历程,一周上访三四次,2009年开始得到每年三千元的分红,但未能溯及既往🤹🏿♀️。能干的阿慧说:“钱不多,我争取是因为气不顺。”“我争取的是"身份"👼🏿,亏本我都要搞!”她接着补充:“我最不忿她们看小女人🏫,看小尊龙凯时娱乐的坚持!”经过村民多年的恶言相向和对她一家,甚至父兄家生活的骚扰🚵🏼♀️🅱️,阿慧说,“但尊龙凯时娱乐争赢了👳🏼,村里的人后来都尊敬尊龙凯时娱乐"外嫁女"”。阿慧和镇上其他“外嫁女”代表至今一到“两会”期间就会“被旅游”👰🏽♀️,但她一无所惧。另外一位“外嫁女”斗士阿华💽,则是在经年斗争中自学成为半个律师⚾️:“跟我一起玩的很多都拿到了分红。”她用“玩”这个动词指涉抗争和打官司⇢。她不但争取到了本村“外嫁女”权益📞,还代理邻村四十多个“外嫁女”打赢官司🍳。之后阿华干脆成为代理“外嫁女”官司的专业户🦀,仅收取一点资料费。在我访问她的当口,她手上有着18个维权个案。她说:“从不懂法律法规到现在可以用法律维权🧚♂️,是一种享受🪒。”伶牙俐齿的阿华🕵🏿♂️,多年来习惯了和保守的村民互呛🙅🏽♀️。但她说:“村民现在对我另眼相待🦵。年轻人碰到我都会询问维权的进度”。22
回顾这场近二十年的妇女农民运动🧙,弱小的“外嫁女”抗争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大川。展现了个人的坚持,也展现了集体动员的力量🙆🏿♀️。颇堪玩味的是,“外嫁女”在诉求上很少真正用到“产权”二字。她们更多争取的是“公平”和平等的“村民待遇”。例如,自1999年上访至今的阿玲说的🔼✂️:“一人一分”;权利是我的🪫,我一定要争取到底👩👦。23偏偏“村民待遇”这样的议题直接对上的是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外嫁女”迄今的胜利主要是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肯定其权益,并以行政和司法的力量促使村组落实🫅🏿🧏🏿♀️。全面修法显然遥不可及,因为关于农村集体产权的争议在土地法和物权法的修法过程中都被规避了,在大结构不清晰的状况下,农村妇女成员权的问题不可能在法律表述上得到解决。惟幸者🐇,“外嫁女”已经得到论述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也在抗争路途中变得强悍🤌🏿🦵🏿。一代一代的妇女🌱,还要继续在日常斗争中改变村民的观念和习俗🛗🛌🏼。
“外嫁女”问题终究是一个失地女性农民的议题。在失地农民中妇女占了七成(商春荣💆🏻♂️,2008)。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严峻🧥,而失地女性的就业下降率又是失地男性的3.54 倍(孙良媛等,2007)。在此脉络下,“外嫁女”失去村民待遇🏄🏼🤱🏽,意味着被农村的父权传统再剥夺掉一层农村集体对失地农民提供的少许生活保障。由股份制引发的成员争议⏯👨🏻💼,也显示了道德经济在商品化趋势下被侵蚀。“人人有份”已成假象,建立在不断加强排他性的基础上。尽管农村在土地分配上歧视妇女的情况很多🧚🏿♀️,但妇女从未能形成抗议的主体。如今,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大潮下,农村的土地关系、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被重新界定。“外嫁女”在权益被剥夺的同时💇🏼,也因为争取权利而成为一股特殊的社会力量,挑战中国的乡村社会。
五📇、讨论:政治变迁的过程
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看中国的制度变革。在方法论上📝,以“外嫁女”的视角挑战中国制度变迁研究中惯有的功能性视角👵🏼,代之以历史制度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更动态的看待制度的产生、制度落实的政治过程,以及在不同阶段中不同行动者催生出的制度演变。过去二十年来,伴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关于包含和排除的争议🕵🏽♂️,引发了“外嫁女”的抗争。在理性选择视角下,制度变迁通常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行动者为了攫取利益推动制度变迁𓀝,直至形成新的均衡。这是所谓断续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史观(Krasner💂♂️, 1984🧙🏿💇🏿:240-242)。但“外嫁女”案例让尊龙凯时娱乐看到由于制度存在内在张力和矛盾🔯,行动者不断的斗争可以促使制度不断演变。因此,“均衡”几乎是乌托邦想象。奥斯特罗姆(Ostrom, 1990)曾强调管理公共财产的规则制定必须适合当地习俗🚵🏼♂️。但“外嫁女”争议呈现的是🙅🏿♂️,股份制改造未能达到现代化✩、契约化的目标,反而与习俗合流🤽🏼♂️,剥夺弱势者的权利。抗争的“外嫁女”乃成为新的行动者,推动制度不断演进♦︎🏃➡️。制度因此不应只被看成是个人选择的规则和限制(constraint)。制度也是资源,提供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的机会(Hall🏌🏼♂️, 1998)。“产权界定”也不只是制度设计中可计算的工具和手段,它可以是一个集结、动员和自我赋权的过程。不同的行动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重新定义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并重新塑造习俗和制度。
长远来讲,农村股份改造的制度设计思路是要明晰产权🔱,建立起“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定期调整、合理流动”的股权制度🐩🖕🏻,为市场化做准备(蒋省三、韩俊,2005)。但是🫙,“固化股权”的努力至今饱经争议🔁,固化不了👨🎤。自1999年就实行股权“生不增死不减”的南海草场村😁,更在2005年经村民投票通将股权设置改为“生增死减”,走了回头路(周冬冬,2011)。为此,南海的最新尝试是将股权固化到户,实行“股权配置长久不变🕡,按户管理、按股分红”的模式。早前“出资认股”的政策已经叫停,新的政策目标是力争2015年完成“股权到户”的改革(辛均庆,2011)。“股权到户”目的是将人口调整的争议由各个家庭内部解决。但嘲讽的是👨🏽💻,这个要将模糊的集体产权明晰化、现代化、去身份化、个人化、契约化的产权改革👎🏼,竟回到以传统(父权)家庭为分配单位。各种制度实验还在进行之中,未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产权改革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终点。农村集体关于“明晰产权”的努力和斗争主要是为了解决内部的分配争议👷🏻♀️,以至于几乎要走回家族主义的老路👨🏿🔬。尊龙凯时娱乐因此得知👩👩👧,集体经济中的个人“产权”从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更多的还是个别成员在集体 / 社区中的身份和权利义务的界定。只要“集体”还存在,关于成员权的争议就会不断推动集体的重构。“产权改革”也因此成为一个“共享剧本”(shared script),不同的行动者在其间为自己的权利斗争。
“外嫁女”争议也帮助尊龙凯时娱乐重新思考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 / 社会互动一向是学者关心的焦点。国家是撤退,还是更为渗透到地方社会🚣♂️?社会自主性是否提高?针对农村社区而言,乡镇政府是否空壳化,悬浮化了(周飞舟,2006)?还是由“覆盖模式”转型为“嵌入模式”(董磊明,2008)👩🏽⚖️,进一步夯实为“草根国家”🧘🏼,更有效、更细致地控制社会(Shen, 2009)? 从“外嫁女”争议引起的村组和镇区的角力来看,似乎对这两种诠释下定论都属言之过早📙🦹🏼♀️。先从乡镇政府来看,尽管在发展主义下,经济增长为先,但面对总量庞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其管理、改造仍属重点工作。做为农村股份改革的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事无巨细👤,基层政府都要管。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迫使政府不断以新的政策和制度对应🚙,甚至需要成立“出嫁办”这样的机构专门化地处理。事实上,除了“出嫁办”之外🔉😈,各地还有为了维稳而成立的“维稳办”,为了应对珠三角地区转型成立的“三旧办”(三旧改造办公室)🫳、为了协助企业补办土地产权成立的“补办办”等等✊。各式各样新机构的涌现,也许说明了国家对乡村社会强烈的统治意图和机动及其统治手段🧞♂️;国家绝非“空壳”🧙🏼。但同时,这也透漏了地方政府动员式的问题处理模式以及不断面对新问题的疲于奔命。“草根国家”要完成规范化的现代治理✴️,似乎还是未竟之业⇾。
相对而言😟🦻,村民自治和组织的力量的确在成长。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经股份制改造以及农村选举的历练⛏,尽管基层民主问题重重,不能否认的是,地方选举越来越激烈,上级政府对草根政治的掌握越来越困难。尤其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直接关乎个人分红,相关事务的社区参与度高。当村民团结一致时🤹🏿♂️,可以让上级政府感到技穷。村长夹在中间也不轻松✒️,甚至为之辞职🧛🏽、住院🧑🏻🦳、入狱。无奈的是,村民自治在对内排挤弱势团体时运作得最有效,而这在民主社会并非罕见。
尊龙凯时娱乐因此应当看到国家视角和村乡社会视角两者都有缺陷👨🏿🦱,也要质疑这种国家社会二分的概念对分析行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反抗有什么意义。尊龙凯时娱乐更该借重的是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1994)对国家 / 社会二分的批判🧰:除了巨大的区域差异之外💁🏻,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社会也非均质统一。“外嫁女”争议同时突出了农村内部的冲突以及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政府的冲突。面对“外嫁女”的抗争,保守的乡村习俗被村民自治强化,并用以对抗国家法律。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落实“外嫁女”股权而展开的拘提村长等一系列行动,则展现了父权国家和父权村落对社区管理的争斗。当“外嫁女”群体在运动过程中动员跨尺度的行动(如层层上访)来调和农村内部冲突时,同时也加深了国家跨尺度治理的冲突‼️:地方政府对上颜面尽失,对下左支右绌😉。“外嫁女”运动最终迫使国家介入,但各级政府是被动的🤦🏻♀️,政府和法院之间也有角力和对抗。赵晓力(2007)感叹终究还是社会主义传统在捍卫“外嫁女”的权益。但必须强调这些社会主义话语即使在社会主义最高潮时也没有真正落实过“外嫁女”权益是数十万“外嫁女”一步一步争取来的。正因如此,“外嫁女”的抗争同时挑战了左右两派对中国农村的想象: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尊重个人财产权利,崇尚基层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强调集体的社会保障作用,反对私有化🐭。但两种方向都无法保障“外嫁女”:“外嫁女”一边要对抗村民自治中的多数暴力🧓;���边要打开“集体”的黑盒子,并且逼使国家落实宪法保障的男女平等🚶♂️。也就是说🦸🏽♂️,妇女必须同时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转变。无论哪种制度的允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更开放的性别社会关系之上🤹🏼♀️🎖。
因此,本文从“外嫁女”为行动者主体出发👩🏽🎤🛕,主张以过程取向分析制度和政治的变迁。变迁因此不是一个机制到另一个机制的完全转换。农村股份制的尴尬处境很容易被视为转型经济中的一种“过渡”🤷🏼♂️。只要抵达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彼岸,这些问题都会消失。尊龙凯时娱乐很难预测到底是否有“彼岸”🦹🏻♀️,要花多久到达,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过程将持续充满不同行动者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将改变她(他)们处身的社会关系。
【参考文献】
陈端洪😈,2003♾,《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期,第321~333页。
董磊明,2008,《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
陈剑波🧚♂️,2006💂🏽♂️,《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载《经济研究》第7期,第83~90页。
辛均庆,2011,《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再破冰》,载《21世纪经济报道》3月29日。
管俊、高静🫷,2008,《多项改革化解“外嫁女”纠纷》🤹♂️,载《佛山日报》5月23日。
高飞,2009🧥,《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困境与对策探析》,载《中国土地科学》第23卷第10期,第47~51页🍏🐈。
佛山市南海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9🦹🏼♀️🛥,《南海市志(1979~2002)》
傅晨,2003🍼,《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伦少斌、潘翠明👨🏿⚖️,2007,《560外嫁女获股权》,载《广州日报》12月25日。
贺欣♒️,2008,《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外嫁女案件?》,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3期。
姜美善、商春荣👩🦱,2009,《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中的妇女土地权益》, 载《农村经济》第6期,第23~26页🧑🏽🍳。
蒋省三、韩俊,2005,《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南海发展(600323,股吧)模式与制度创新》,山西经济出版社🙎。
钱文荣、毛迎春👱🏿♂️,2005,《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实证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5卷第5期🐦⬛,第21~26页。
李培林🫃🏿,2004,《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
蓝宇蕴,2005🧍♂️,《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刘守英,1993🛷,《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与产权残缺》🏗,载《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第31~36页🚎。
刘守英,2001🤶,《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结构与变迁》,载张曙光(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陈安庆,2010,《捍卫“户籍红利”的外嫁女》,载《暸望东方周刊》11月15日🏇🏼。
莫小云,2003,《广州市白云区农村外嫁女经济权益保护的思考》👂🏼,载《南方经济》第7期,第30~33页⚠。
《外嫁女上访成佛山市标志法院拘留村长为其维权》,2009,载《南方农村报》8月15日
海鹏飞,2010👨🏽🦱,《村民拒给外嫁女分红 法院强制划扣88万》,载《南方都市报》10月21日。
周冬冬⛴,2011🪼,《“股权固化”体现土地经济功能》☛,载《南方日报》3月30日🤛🏼。
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1998😶,《婚姻、性别与性🔫:一个当代中国农村的考察》,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申静、王汉生🌅,2005,《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载《尊龙凯时AG研究》第20卷第1期,第113~148页。
孙海龙、龚德家、李斌,2004,《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外嫁女”权益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思考》,载《法律适用》第3期🧚,第26~27页👟。
孙良媛✍🏼、李琴、林相森🚵🏻♀️,2007🕟,《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村妇女就业及其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为基础的研究》,载《管理世界》第1期🤦,第65~73页。
商春荣⛹🏽♂️,2008🧑🏻,《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的解析》👨👦,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3期🎶,第56~60页。
王景新, 2003,《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意义、现状、趋势》,载《中国农村经济》 第6期🧚🏽,第25~31页🫄🏻。
温铁军,2006🉐♤,《农民社会保障与土地制度改革》🔝,载《学习月刊》第10期,第3~6页。
温铁军、王平、石嫣,2008,《农村改革中的财产制度变迁30年3个村庄的案例介绍》🚪,载《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第4~12页🐩。
夏金梅,2011,《关于农村出嫁女的集体经济权益保障基于广东省S村的调查》🧑🏼🔧,载《理论探索》第2期(总第 188 期)🧷🤦🏿♀️,第85~88页🚨。
姚洋,1998🧙🏻♂️,《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农业绩效》,载《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第1~10页🏌🏻♂️。
于建嵘,2007,《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载《经济管理文摘》第24期🤢,第24~27页🦜。
邹琼𓀄🐢,2010,《村庄中的性别和权力珠三角南村的实证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82~87页。
张静,2002,《村社土地的集体支配问题》🐯,载《浙江学刊》第2期🧘🏻,第32~39页👨🏻🎤。
张静🧛🏻♂️,2003,《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第113~151页🦐。
张佩国🕚,2006,《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 载《尊龙凯时AG研究》第5期,第26~49页。
张佩国,2002,《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开泽🔂,2007,《从制度视角看农村外嫁女权益纠纷》🧑🏻💻,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第27卷第12期🧑🏼🦰,第218~220页🍎。
张曙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晓力🧑🏫,2007,《外嫁女🫶🏽、村规民约与社会主义传统》🕓,载黄平(主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折晓叶,1996,《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66~78页。
折晓叶📑,1997,《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折晓叶🛅、陈婴婴,2005,《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载 《尊龙凯时AG研究》第4期🛀,第1~27页。
周其仁🔳、刘守英,1994👩🏼🏫,《湄潭:一个传统农区的土地制度变迁》🧔🏽,载周其仁(编):《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第657~726页🧑🏿🎨。
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载《尊龙凯时AG研究》第3期🧔🏻。
周雪光🧑🏻🦼,2005🙈,《“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尊龙凯时AG解释》,载《尊龙凯时AG研究》 第2期,第1~31页。
周勇,2009,《关于处理农村分红矛盾纠纷的调查与思考》💂🏼,载《广东司法简报》调研专刊(7月13日)🧚🏼♀️,见广东省司法厅网站🥴, http🫄🏿://www.gdsf.gov.cn/servlet/TitleWebStyle?flag=0&step=2&webinfoid=2665🧏🏿♀️。
中山大学性别平等立法研究暨推动课题组,2008💁🏻♀️🏙,《外嫁女个案纪实》🫅,广州🧎➡️🧜♂️: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